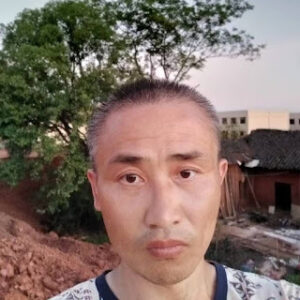张云帆:我给人民的自白书
感谢北京大学钱理群、孔庆东、张千帆、李零、陈波、柴晓明、宋磊等多位师长和张耀祖、李民骐、汤敏等海内外北大校友;感谢黄纪苏、旷新年、祝东力、秦晖、于建嵘、徐友渔和宋阳标、陈洪涛、范景刚等400余位社会各界的老师、朋友们!
感谢你们的仗义执言,使我得以重见天日。
请原谅我不能一一拜访,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!
我是2017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审的。但结束了30天的刑事拘留和14天的监视居住之后,我发现,对自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我无法把这一页掀过去,只能直面这种考验。
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,是学霸,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。
然而,马克思主义者和“毛左”,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,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。
我能看到,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。
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,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,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,风雨飘摇;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,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,其生命轨迹,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,献了终身献子孙。
“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,失业的订单/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/我咽下奔波,咽下流离失所/咽下人行天桥,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/我再也咽不下了/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/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/耻辱的诗”
崛起背后,阴影长长,一寸光环,一寸血色。
诗人坠下高楼,信念冉冉升起。
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,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。
网上某些传言是真实的,北大读书期间,我确实曾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。我和大学里的同路人不仅在读书会上研读那些理论著作,弱势群体所在之处也会有我们的身影。经过数不清的唱歌跳舞讲新闻放电影英语班,渐渐我发现,无论走到哪里,都有校工大哥大姐和我打招呼——在打饭的时候,总会多那么一勺。
毕业后我来到广州,除了参加工作,自力更生之外,生活没有什么不同。说得高尚一些,我在广东工业大学中继续一点一点践行着理想,其实无非是继续参加读书会和志愿活动。
在被拘捕的那次读书会上,我们讨论了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问题 —— 涉及重大历史事件、劳动者地位权利等等。我们讨论作为青年人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。我承认,我们还谈到了29年前有大学生参与其中的那场风波。
一定有人会好奇,我的言论是否真的过激?
当然不如报纸电视教科书那么标准化,如果按照上述标准,承认社会有问题就足够“过激”了,讨论“如何解决”无疑更“过激”。
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,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,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?
这是权利!
宪法赫然写道,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”,若言论有“过激”,那“自由”毫无意义!
不过,如果拘捕我的原因是“讨论社会问题”,那至少让我感觉尚且受到了严肃对待。11月15日带走我的时候,警方看我从事教育行业便给我安了一个“非法经营罪”。或许因为过于滑稽,正式刑拘时换成了“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” —— 我一个24岁的青年竟然威力如此巨大,能够导致一所上千亩的大学“工作、生产、营业和教学、科研、医疗无法进行”?
这不正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
我被要求承认有密谋活动——真的有什么密谋组织吗?
读书会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?广场舞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?读书会上种种必要的简单分工,难道就是什么“密谋组织”吗?
我还被要求承认自己有“极端思想”,保证以后再也不参加读书会,被要求“供出”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。
看守所冰冷的地板,八小时连续不断的审讯,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,太多太多精神折磨,难以言说。当被告知更多的人会因我被抓捕,父母会被连累的时候,我承认,我没能顶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,只想快点了结,哪怕自己进监狱,只要能让其他青年和家人得到安宁。所以,我妥协了。
没有料到随后会被取保候审。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岁月让我话都说不清楚,思维也十分迟缓。
经过十几天恢复,我终于回过神来 —— 更没有料到:我的妥协竟如此苍白无用!
虽然这次因读书会受到牵连的孙婷婷、郑永明、叶建科几位青年也与我一同取保候审,但左翼青年徐忠良、黄理平、韩鹏和我的女友顾佳悦却被网上追逃!我们的罪名并没被取消,依然是待罪之身 —— 尤其是徐忠良四人,他们现在就是被网上追逃的“逃犯”!
我不敢想象,他们四人现在处于什么境地。一闭上眼,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在国统区,那呼啸的警车、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缉令的密探追捕那些东躲西藏、找不到一处存身之地的进步青年们!
而我,也可以沉默不语——按警方指示,“谨言慎行”,回归“正常”的生活,放上一张平静的书桌,躲进小楼成一统,从此去做一个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但却要一辈子背负不属于自己的罪名,一辈子远离读书会和我热爱的劳动人民。
更何况,我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左翼青年被四处追逃拘捕!
并非出身名校的他们不会像我这么幸运,能在大家的呼吁下走出来 —— 他们连广州都出不去,更没有当年的延安可以投奔,只能去经历何其漫长的监禁岁月!
我走出了监狱,可是套上了良心的枷锁;逃脱了法庭,但永远遭受道义的审判。
甚至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但自此之后,任何理想青年都可以被抓捕,任何读书会都可以被定罪,任何志愿活动都可以被控制,理想精神不可触碰,言论自由极端廉价,马克思毛泽东都是笑话!
要多么无情无义,才会在此刻低头?!
我听到许多“适可而止”“中庸之道”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。
我当然能理解这是对我善意的关怀。但我怎能躲开我的同志,去做那个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?
更不必说,“言论自由”受宪法保护,无所谓适可而止;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,从不是“中庸之道”;我“退一步”让自己“海阔天空”,但我的同志却要跌下万丈深渊!
—— 同时跌下万丈深渊的,还有所有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全部尊严。
与其忍辱偷生,不如迎头面对!我只能说出真相,再不妥协;即便再次经历牢狱之灾,也远胜眼前这苟且的煎熬。
一切善良的人们啊,恳请你看到 —— 你为之奔走的人在这里,他不会辜负你的呐喊。
他将昂首挺胸,面对暴风降至。
他已做好准备!
张云帆
2018年1月15日
2017年11月15日,张云帆等人在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学生自发进行的读书会时,保安突然闯进教室,教室前后被头戴钢盔的学校保安和治安联防队堵死,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部分青年带到派出所,张云帆与叶建科两人因没带身份证件,次日以涉嫌“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”被刑事拘留。随后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、警方约谈警告。读书会解散。
根据张云帆和叶建科随后发布的自白书,读书会当时讨论了时事热点问题,如暴走大事件视频下架,言及舆论不自由,期间涉及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和工人权益变迁问题。
自始至终,青年的自白书都表明他们所有可能“涉罪”的行为只是组织或者参与校园读书会和后勤工友的文娱活动,这些行为没有触犯刑法,也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规定的“情节严重,致使工作、生产、营业和教学、科研无法进行,造成严重损失”。然而,番禺警方至今也没有公开更多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究竟有何罪行。
2017年12月5日,警方闯入读书会发起者、大学毕业生郑永明住所,将其带到派出所进行连续审讯,随后将其定为“主谋”,郑永明遭到刑事拘留。
2017年12月8日,晚10点左右,警察闯入读书会参与者孙婷婷的出租屋,在未出示证件的情况下搜查其住所,后将孙婷婷带到派出所,威吓其交代其他成员的情况。次日,警方再次搜查并带走孙婷婷的大量私人物品,当晚对孙婷婷进行刑事拘留。
依照法律规定,刑事拘留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:其一,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(即正在实施犯罪的人)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(即有证据证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);其二,具有法定的紧急情形之一,如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犯罪。
且不说对于12月9日已经不在读书会“犯罪现场”“实施犯罪”的郑永明和孙婷婷,警方是否果真有证据证明其是“重大嫌疑分子”,两名青年被抓时也并没有发生刑诉法所规定的“紧急情形”的任何一条。警察仅仅因为系统“只能提交一个拘留”,就给孙婷婷办成了刑事拘留,并且突破刑事拘留期限最高14天的法律规定,让孙婷婷在看守所待了26天之久。
2017年12月15日,警方对张云帆和叶建科的刑事强制措施变更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。在此期间,张云帆被关在秘密处所。
2017年12月21日,《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“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”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》在网上公开发布,信中首次向社会披露了张云帆参与读书会“因言获罪”的遭遇,并呼吁公众声援,包括钱理群、孔庆东、于建嵘等在内的多位知名教授学者和大量社会人士参与联署。联名信屡次被删,但联名队伍不断扩大。众多公众号发文呼吁支持。
公开信的发表使得事件逐渐传播开来,引发各界关注讨论。期间,《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张云帆其人》等与张云帆相关的信息公开,显示其在校期间成绩优异、热心公益。
联名人数的不断增加、众多知名人士的参与、学生的讨论声援和国外媒体报道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,番禺警方原本定为6个月的监视居住在执行14天后就告终止。
2017年12月29日,张云帆和叶建科在14天的监视居住后获取保候审。
2017年12月30日,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发表文章《言论自由不分左右》,从捍卫言论自由的角度,支持左翼青年张云帆。
2017年1月4日,孙婷婷和郑永明被取保候审。
2018年1月15日,张云帆在其微博公开发布《我给人民的自白书》,说明事件原委,称警方强行要求自己交代莫须有的“密谋活动”和“密谋组织”,正可谓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自白书中指出徐忠良、韩鹏、黄理平和女友顾佳悦4人仍被警方追逃,呼吁公众为蒙冤获罪的青年声援,自己已经做好面对危险的准备。